2020年12月24日,国药中生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Vero)上市申请正式获得NMPA受理。世界的另一边,辉瑞/BioNTech和Moderna的两款新冠疫苗(mRNA)也先后获得FDA的紧急使用授权(EUA)。中美两国新冠疫苗研发的领跑者们已经撞线,所用时间
2020年12月24日,国药中生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Vero)上市申请正式获得NMPA受理。世界的另一边,辉瑞/BioNTech和Moderna的两款新冠疫苗(mRNA)也先后获得FDA的紧急使用授权(EUA)。中美两国新冠疫苗研发的领跑者们已经撞线,所用时间还不满一年。
这前所未有速度是如何达成的?近期,美国《连线》(wired)杂志对话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疫苗研究中心(VRC)主任讲述新冠疫苗背后的故事。我们编译了其中部分内容来呈现美国“Operation Warp Speed”(“曲速行动”,美国加速研制和生产新冠疫苗的政府资助计划)下企业选择、国家力量、社会责任之间是如何实现平衡并共同完成新冠疫苗研发的。
疫苗正在给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带来曙光。
而这背后是惊人的科学技术成就:在美国,从新病毒到新疫苗大约只用了12个月,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并且应用了最新的疫苗技术。
《连线》认为功劳离不开美国各地的研究合作者们在研究冠状病毒上花费数年时间所做的努力,其中一份来自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疫苗研究中心(VRC)主任约翰·马斯科拉(John Mascola)的实验室。
正是马斯科拉的VRC将mRNA带到了Moderna。他和VRC的同事正确地预见了即将到来的事情,并知道如何为此做好准备。
“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疫情会是什么。它可能是流感的变种,也有可能是多种病原体之一。不过有个简单的办法,你可以去看看过去20年爆发的疫情清单。如果上面有两种病毒属于冠状病毒家族,那么对它再次出现你大可不必感到震惊。SARS在2002年,MERS在2012年,在疫病大流行史上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范围”,马斯科拉说。
如今的成果令马斯科拉感到欣慰,“我们一直相信DNA和RNA这些新技术可以在疫苗学和应对疫病大流行中发挥重要作用。很高兴看到这成为现实。”
至于为什么会与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Moderna合作,马斯科拉表示,这得益于双方的互信基础,“我们相信Moderna有非常强大的科研能力来制造RNA疫苗”。而这一基础的获得,更多是来自双方从2017年开始的针对塞卡病毒的合作和对冠状病毒等传染病疫苗研究上的共同兴趣。
马斯科拉坦诚其中的运气成分。“对于原始的SARS和MERS我们都能成功通过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来制作疫苗,所以我们有信心。但也并不确信当另一种冠状病毒来袭时我们是否可以应用相同的结构来稳定突变。我们只能试着观察病毒和刺突蛋白的遗传序列,将我们最初对SARS所做的工作转移到新的SARS-CoV-2中去。结果是,在这些突变中立即起了作用,这让我们在比赛中取得了领先。”但最核心的还是基于对冠状病毒的研究积累。
“我们确实很幸运,但慎重来讲,我们对冠状病毒也足够了解。”
以下对话的节选:
Q:早在COVID-19出现之前你就提倡基于mRNA开发新疫苗和新的制造方法,最近的几周你是否感到得到了某种证明?
马斯科拉:结果的确让人欣慰。不仅仅是证明,我们一直相信DNA和RNA这些新技术可以在疫苗学和应对疫病大流行中发挥重要作用。很高兴看到这成为现实。
Q:VRC在mRNA和刺突蛋白上的研究最终是如何由一家相对较小且缺乏经验的制药公司Moderna来进行开发的?
马斯科拉: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在2017年或者更早对塞卡病毒开展研究时就开始了,在传染病疫苗上强烈的共同兴趣让我们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Moderna对寨卡病毒的研究很感兴趣,他们从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管理局(BARDA)拿到一些资助,并且希望找一个科学合作伙伴来进行疫苗的设计。而当时VRC也考察了许多有能力生产RNA疫苗的公司,我们相信Moderna有非常强大的科研能力来制造RNA疫苗。之后在共同探讨其他感兴趣的领域时,我们提出冠状病毒或许会是一个富有成果的领域。
Q:我想这不单纯是“猜测”更是基于一个好的“假设”对吗?也就是说,冠状病毒将成为一个问题。
马斯科拉::我们其实做了两手准备。没有人知道下一次疫情会是什么。它可能是流感的变种,也有可能是多种病原体之一。不过简单的办法,你可以去看看过去20年爆发的疫情清单。如果上面有两种病毒属于冠状病毒家族,那么对它再次出现你大可不必感到震惊。SARS在2002年,MERS在2012年,在大流行史上这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范围。
我们与Moderna一起设计了MERS的早期临床前疫苗,因此能够测试我们的mRNA是如何工作的,并且有能力对RNA带给人体的免疫反应进行一些设计测试。当发现COVID-19病毒是冠状病毒时我们已经奠定了很多基础。
Q:但你是否担心在MERS上刺突蛋白的研究无法应用到COVID-19病毒或SARS-CoV-2上?
马斯科拉:对于原始的SARS和MERS我们都能成功通过刺突蛋白来制作疫苗,所以我们有信心。但也并不确信当另一种冠状病毒来袭时我们是否可以应用相同的结构来稳定突变。我们只能试着观察病毒和刺突蛋白的遗传序列,将我们最初对SARS所做的工作转移到新的SARS-CoV-2中去。结果是,在这些突变中立即起了作用,这让我们在比赛中取得了领先。
Q:所以,这其中有运气成分。
我们确实很幸运,但慎重来讲,我们对冠状病毒也足够了解。
现实是科学界为刺突蛋白所做的第一个设计就成功了。不过让我们来做个假设,如果我们做了一个疫苗但效果不是很好会发生什么?我们可能不得不回去做第二代设计,为此将损失三到四个月。想想看那时世界将会怎样。塞卡病毒便是如此。VRC与Moderna一起设计了两种类似蛋白的设计(不是刺突蛋白,而是病毒表面的蛋白),第一款临床效果不太好,没有诱发非常好的免疫反应,直到第二个才做到。这在科学界很普遍。
Q:为什么会有“Operation Warp Speed”疫苗资助计划?它的任务似乎是VRC应该做的?
马斯科拉: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不同。我当时赞成创立资助计划,正因为我是疫苗中心的负责人,我清楚我们可以做什么和自己的局限。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有能力开发一款疫苗并且进行早期临床,但没办法将其商业化或大规模生产。NIH不像BARDA那样资助后期研发,需要找到私营公司来进行合作。此外,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政府工作多年,此前也曾见过传染病疫情肆虐,因此很清楚当遭遇这样一个严重疫情时政府内部应该把资源整合在一起来共同应对。
Q:但是为什么要从企业而不是政府或学术界找一个主导者呢?
马斯科拉: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建议找一个外部顾问。当你引入Big Pharma 的人来运作项目时你就能得到他们的意见,这对公众来说是一种增值。我在VRC与企业打交道的经验是,如果你想和企业合作就需要了解他们的动机。我是一位政府研究人员,我理解自己的动机。辉瑞表示不与我们合作决定自己做。Moderna 与我们合作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每个人都这么说怎么办?这才是我思考的问题。
Q:你曾表示不同药企进行的新冠疫苗临床试验和收集到的数据应该进行统一。在我看来现在这并没实现。各个药企的实验不仅有不同的临床终点而且都没有进行头对头试验。药企更愿意自己推进实验而不依靠独立的第三方研究人员。您对此是否有信心?
马斯科拉:关于这一点已经进行了大量讨论。正如你所知道的,如果资助的实体是BARDA,通常来说BARDA会以更传统的方式提供资金:按照合约提供资帮助企业开发疫苗,同时要求企业报告进展和里程碑。这种情况下,每个公司都做自己的事情并不需要协作。
另一种方式是一切都由政府控制,每个公司按方案分配任务。这种被称作母方案(master protocol)模式此前也曾被广泛讨论过了,在某些情形下这也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不过对于新冠病毒而言这些都很难实现。首先,疫苗问世的时间点不同,所以永远无法真正实现头对头的试验。因为传染病不断变化至关重要的对照组也不断变化。第二,疫苗试验规模巨大,比任何一个实体所能协调的规模都要大。第三,由于疫苗商业化向FDA提交上市许可所需的数据必须通过一家公司来进行申请。因此从速度和效率的角度让FDA认可的一家公司作为试验的责任主体更好。
不过“曲速行动”对试验也提出了一套严格的要求。他并非一个母方案而是一系列所谓的协调方案。它们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如果您退后一步看到它们的设计都非常相似。监管方即由NIH创立的数据安全监测委员会(DSMB)对计划中的每个试验一视同仁。这些协调都是我们所推进的。
Q:但是辉瑞并没有得到warp speed的资助,所以他们有着不一样的DSMB。这会不会为之后的批准和对比带来问题。
马斯科拉:有件我想你已经知道的事非常重要。即使是由“曲速行动”资助的公司,他们的疫苗在提交上市许可或EUA时都会提交给FDA审批。VRC不会扮演FDA角色。
另外我想说的是,辉瑞始终与“曲速行动”保持了紧密联系。我感觉他们正在做的试验与Moderna的试验十分相似这也将使申请变得更加容易。答案的另一部分是,除了辉瑞参与数据安全监测委员会的其他公司还会贡献他们的数据。因此,我们可以一起查看所有试验的数据。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将这些试验结合起来我们将可能从中会学到很多东西,而不是一个个单独的试验。
Q:仅有三期数据就可以做到这些吗?就算辉瑞和Moderna并没有定期测试那些无症状的人?他们有在收集你所需的数据吗,还是需要等到疫苗上市后?
马斯科拉:不,三期试验还在进行中。辉瑞和阿斯利康都在收集大量关于所谓“病例”的样本和信息。而每个参加试验的感染者将成为一个病例。这些详细的实验室数据和医学信息都是三期试验记录的一部分。
Q:但是那些非感染者的信息呢?
马斯科拉:为此我们会进行一些相关研究,在其中详细研究病例和非病例(已接种疫苗但未成为病例的),以比较他们的免疫反应。以便了解免疫的相关性,每项研究都是如此设计的,这也是被所有公司认可的。
Q:疫苗进入更广泛的人群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是否会针对长期安全问题或免疫持续效力来进行跟踪?
马斯科拉:我认为这是可行的,FDA的确会在产品上市后进行监测。而且EUA并非上市许可,产品在获得正式许可之前都会受到监测,公司也将有责任在履行其EUA时进行详细的跟进。
Q:抛开疫苗专家的身份,你想看到哪些数据?想知道关于新疫苗的什么信息?
马斯科拉:其中有很多关键数据。总的来说,我们知道疫苗在预防有症状的新冠病毒方面非常有效。多数人只有在梦中才敢设想94%或95%的疗效,这意味着病毒容易受到免疫系统的影响,我们终将控制疫情。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所有事情。我们不清楚疫苗在老年人群或体弱多病的老年人、或者免疫系统不完善的人群中的效果如何。我们不知道免疫能够持续的时间,会是一年还是两年?我们不知道无症状感染这是否可能被预防。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学习,第一批研究是学习它的关键时机。
最后,我们真正想知道的是免疫的相关性,它是免疫系统的关键参数和保护机制。免疫系统总是协同工作的,因此通常当我们识别某些关键参数并提升它可以为我们带来保护。
Q:你是否担心正在和将要进行的疫苗临床试验所带来的影响?一款疫苗已经奏效但仍要继续进行试验时,那些对照组的志愿者们将会怎样?
马斯科拉:我认为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们拥有了远超预期的疫苗,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去弃考这样的伦理问题:当你的疫苗已经取得不错的临床证据,随机对照试验还应该进行多久?怎样确认这是否是好证据呢?
我觉得并非是某个公司的新闻稿来决定的,而是FDA看到数据并表示“我们看过主要试验数据了,的确有95%的有效性。”并且FDA批准紧急使用授权。然后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将疫苗提供给研究的安慰剂治疗人群?我认为这将是未来几周FDA疫苗及相关生物产品咨询委员会(VRBPAC)会讨论部分。
Q:你已经见证了过去一年疫苗开发的进程,其中又有怎样的启示?不只是对于疫情大流行还包括一般的传染病。
马斯科拉:回头看当初在用新技术来研发疫苗时会有各种担忧。现在我们已经我们已经证实mRNA疫苗可以起作用并且可以迅速投入使用。我认为腺病毒技术也可能提供相当好的保护,这些新技术很可能也是可行的。
另一点让人感到鼓舞的是这证明了基于科学结构的疫苗设计是可行的。同样的概念也开始针对呼吸道病毒等其他情形进行测试了。
现在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全球监测体系。这套体系可以使用现代技术进行测试让我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还需要更好的全球临床能力来推进大规模的试验。美国政府可以提供100亿美元、120亿美元来激励药企,但是世界其他地方呢?我们如何搭建临床试验所需的基础设施?
Q:人们都在说我们用了一年时间就得到了新冠疫苗,但我知道这并不准确。我们花了近二十年才真正了解冠状病毒。但如果下一场疫情不是冠状病毒呢?
马斯科拉:病毒的确可能会从那些我们没有做好准备的病毒家族中出现。我们知道世界上大约有20个主要的感染人类的病毒家族,在过去50多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几乎每一次爆发的疫情都来自这20个病毒家族之一。如果我们齐心协力对每个病毒家族进行详细研究、制作疫苗,像我们对冠状病毒所做的一样会怎样呢?我们应该制作一些原型,那么就算出现该家族的表亲,一种我们从未见过的病毒,至少我们已经为疫苗设计奠定了基础。之前人们会认为这是一笔很大钱,但在经历过大流行之后现在这已经算是一笔小投资了。
Q:你是指如果一场疫情要花费16万亿?
马斯科拉:正是这样。我不想拿出一些并不完全准确的数据,不过每个病毒家族只需花费2000万美元,就可以制作一个原型疫苗并在进行临床测试。五年十亿的投入在过去会被认为站不住脚。但如今如果能为下场大流行做好准备,这很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本文来源:E药经理人 作者:苏唐 免责声明:该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仅代表作者观点,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医药行”认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如涉及作品内容、版权和其他问题,请在30日内与我们联系
 客服微v信:
客服微v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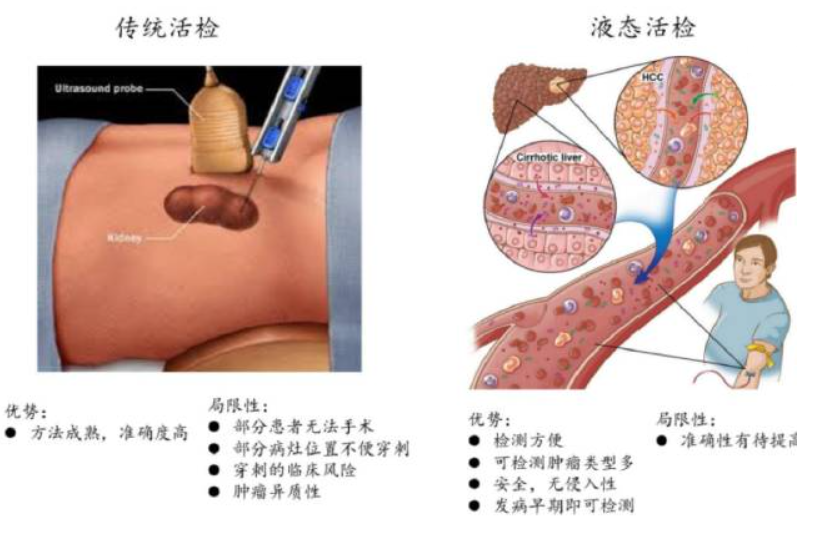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1568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1568号

